猫城记,我和彩云小梦一起写 | 007号张二来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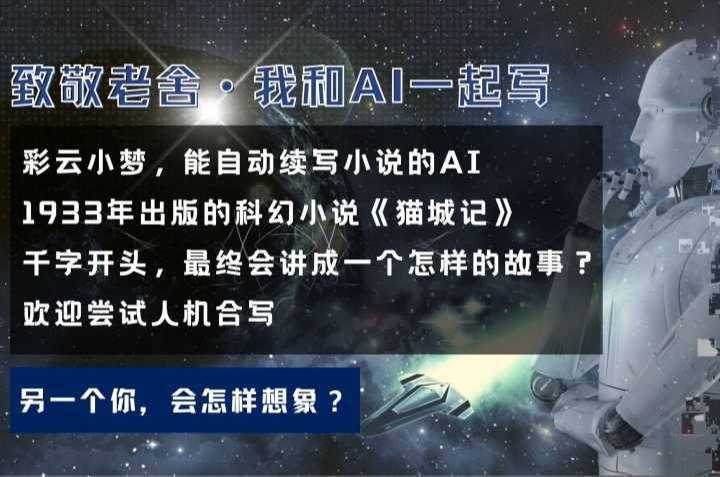
👆 参 与「无界•文学行动」
致敬老舍·我和AI一起写
007 | 猫城记,我和彩云小梦一起写
文 | 张二
注:本文蓝色文字内容为老舍先生所写(《猫城记》1000字开头),橙色下划线内容为用户的AI小梦所写。
飞机是碎了。
我的朋友——自幼和我同学:这次为我开了半个多月的飞机——连一块整骨也没留下!
我自己呢,也许还活着呢?我怎能没死?神仙大概知道。我顾不及伤心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火星。按着我的亡友的计算,在飞机出险以前,我们确是已进了火星的气圈。那么,我是已落在火星上了?假如真是这样,我的朋友的灵魂可以自安了:第一个在火星上的人,死得值!但是,这“到底”是哪里?我只好“相信”它是火星吧;不是也得是,因为我无从证明它的是与不是。自然从天文上可以断定这是哪个星球;可怜,我对于天文的知识正如对古代埃及文字,一点也不懂!我的朋友可以毫不迟疑的指示我,但是他,他……噢!我的好友,与我自幼同学的好友!
飞机是碎了。我将怎样回到地球上去?不敢想!只有身上的衣裳——碎得象些挂着的干菠菜——和肚子里的干粮;不要说回去的计划,就是怎样在这里活着,也不敢想啊!言语不通,地方不认识,火星上到底有与人类相似的动物没有?问题多得象……就不想吧;“火星上的漂流者”,还不足以自我慰藉么?使忧虑减去勇敢是多么不上算的事!
这自然是追想当时的情形。在当时,脑子已震昏。震昏的脑子也许会发生许多不相联贯的思念,已经都想不起了;只有这些——怎样回去,和怎样活着——似乎在脑子完全清醒之后还记得很真切,象被海潮打上岸来的两块木板,船已全沉了。
我清醒过来。第一件事是设法把我的朋友,那一堆骨肉,埋葬起来。那只飞机,我连看它也不敢看。它也是我的好友,它将我们俩运到这里来,忠诚的机器!朋友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我觉得他们俩的不幸好象都是我的过错!两个有本事的倒都死了,只留下我这个没能力的,傻子偏有福气,多么难堪的自我慰藉!我觉得我能只手埋葬我的同学,但是我一定不能把飞机也掩埋了,所以我不敢看它。
我应当先去挖坑,但是我没有去挖,只呆呆的看着四外,从泪中看着四外。我为什么不抱着那团骨肉痛哭一场?我为什么不立刻去掘地?在一种如梦方醒的状态中,有许多举动是我自己不能负责的,现在想来,这或者是最近情理的解释与自恕。
我呆呆的看着四外。奇怪,那时我所看见的我记得清楚极了,无论什么时候我一闭眼,便能又看见那些景物,带着颜色立在我的面前,就是颜色相交处的影线也都很清楚。只有这个与我幼时初次随着母亲去祭扫父亲的坟墓时的景象是我终身忘不了的两张图画。
我说不上来我特别注意到什么;我给四围的一切以均等的“不关切的注意”,假如这话能有点意义。我好象雨中的小树,任凭雨点往我身上落……
不行,这样太不公平了。我一定要把它们全看见,我要把它们一点一点重现在我眼前,重现在我的世界里......我要让它们再次成为我的一个依靠。
我不甘心的再次睁开了双眼。四围的影线又一次出现了。但是这次,影线中的景物比刚才还少了,只剩下一片模糊。这是一片灰白色的空间。另外再加上一些毛茸茸的半透明蒲公英。我不认为它们是蒲公英,只是看上去像,是一种视差作用,它具有安神的效果,作用于我身上恰如其分。
一场海难总会留下一点残骸,现在这残骸便是我。阳光,海难过后的阳光也好,风也好,海滩也好,是对这残骸的温柔,就像那些基督徒所说的,上帝的怜悯。现在,对于我这悲惨的尤利西斯,上帝赐以蒲公英。
当蒲公英飘浮在这片灰白色空间,以迥然不同与地球力场的存在形式,使我确切地意识到已经告别了故土,不同于童年时期出门做客,——哪怕是做客呢,也会让每一个孩童心怀忐忑,担心再也无法回到家中,即便做客的地方离家只有六公里,也像是已经去到了异国他乡,没有熟悉的房屋和树,没有指向家的道路和小石桥,亲戚家里永远是灰蒙蒙的一片黯淡,要是点上灯,那灯光也虚弱得叫人心酸。所以现在是否也因为同样的缘故,我才会认为这火星的世界也暧昧不明呢?
我想着,从残破的行李舱找到火星飞行器,开始向火星的东北方向飞去。
时间飞逝,不知多久。火星东南方向,有一片蓝色的湖泊。火星的东南方向,也就是地球的北方,我们的故乡。我记忆中,我曾经在一些杂志和电视中看到过。这片湖泊的名字叫做"蓝湖",是由蓝水晶组成。蓝水晶!我的妈妈!这片蓝水晶是不是与我父亲的棺椁有关系?我要找到它!
但是现实并没有给我答案。我继续飞,直飞到湖泊边上。
这时的湖泊矜持地紧绷着,亡友提到它的时候我就在琢磨,我应该到这里来。他倒没有很推荐,这里不适合初来者,也就是说,在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好火星生存小技能的时候,贸然来这里会很危险。它对待初来乍到的客人并不友善,比如说极度的低温,突然的结晶或崩碎,以及湖中的火星生物,它们在水晶之间游走,吸食空气中的水晶凝结物,所以它们天然具有毁灭地球生命的能力,对于暴露在空气中的地球人是致命的。当然,有人曾经试图将它们带去地球,它们同样也死于地球的氧气,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有更高明。 在我看来,这是一趟宿命之旅。火星,蓝水晶,父亲。告别地球对于大多数地球人来说都不是太愉快的事情,于我则正好相反。谁曾经历过妻子离家出走和母亲漫长的离世,都不会再对旧有的生活抱有太多留恋,世界是碎裂的,炮弹袭击之后的墓场,四周都是触目惊心的白骨,翘曲在墓碑后面的棺木,它们曾经以为凭借自己的倔强可以抵挡住整个活人世界,不过是痴心妄想。
然后母亲说,我应该到火星来。所以我该如何去理解她呢?是真的交给我一个使命还是分明已经知道我不得不需要一个目标来逃离沉沦?毕竟,除了妻子就数她最了解我了,她对自己儿子到底有多大出息心知肚明。
她从来没有对我提到过父亲的火星,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她说完之后就落入了永恒的睡眠,照护士的说法,体面又安祥地滑了进去,这也算是给我最后的一丝安慰。
关于父亲,她是这么说的,一个好人,只是不太懂得温柔,说话像军人一样直接,做事一板一眼,可是你不要以为那是因为他笨拙,“其实你爸爸一点都不笨。”你试想,一个笨蛋怎么可能进入国家航天局呢,并且成为火星先驱,他是新时代的张骞,哥伦布,啊不对,哥伦布是个唯利是图的野蛮人,那些屠杀印第安原住民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可真算不上是英雄,如果印第安人在天有灵,一定会希望用一场大火报复欧洲,至于他们那个装腔作势的上帝,不过是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包庇犯,也可以一并送上火柱。
母亲说我应该来看看自己的父亲,这里面有一个约定,她跟我父亲的约定,在我还在襁褓时他们就说好了,那时候还没有后来这么便捷的通信,一个约定具有的效力往往更为持久。母亲没有详细说明,那会儿她开始咳嗽,所以我闹不明白,也许她故意在卖关子。总之她提到了水晶湖,认定就是这个地方。她怎么自圆其说呢?在她和父亲做出约定的时候,他们谁也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也不会知道。母亲说的,是火星。而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拥有火星的,因为它是一颗火星,是火星,我知道它,但我从没有亲自到过那儿。这一点上,我跟父亲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是个不喜欢浪费时间的人。所以我不会到火星寻找自己的父亲,也不愿意去。我宁愿自己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地在宇宙空间中前进,我不想到火星去冒险,也不愿意被别人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而现实永远都是如此的鬼使神差,如今我的旅行正好就搁浅在了火星。
在母亲的记忆中,父亲的墓地在蓝水晶湖旁边的一个湖心岛,而且在那个位置,也有着一座火山。那里面的火山岩浆,就像一条条红色的火龙一样,在湖面上奔腾咆哮,那样子,让人胆战心惊,那些喷涌出来的岩浆最终沉淀,就构成了拥有巨大落差的湖底悬崖,同时形成了那个半悬空的湖心岛。
现在我可以确定了——感谢所有为了我的火星之旅而牺牲的伙伴,这使我安心不少。 我让飞行器在湖心岛上降落,一阵风贴着湖面吹过来,几乎将我掀起到空中。我还需要适应这里的引力,以及从过滤器里呼吸不那么纯净的氧气,这是我的同学——了不起的人,他死得那么从容不迫——送我的一件礼物,在它的帮助之下我游历至今,我将通过继续活着来纪念他。
他同样知道湖心岛,像导游那样给我介绍,“你可以想象那是从湖底长起来的参天大树。”他这么说。它的树冠像花椰菜紧密地拼合在一起,所有尝试过的探险都功亏一篑,这个地方的环境是前所未见的,哪怕地球人在开拓外星世界上已有长达两百年的经验可以倚仗。对此我保持只能沉默。任何表明我知道这个地方的话都会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到时候我们就身不由己了,我不喜欢身不由己。
有一种可能,湖心岛是一座纪念碑,通过一种原始的形态,反正你总不可能在火星上立起一根柱子,那样太过明目张胆,并且缺乏想象力。(而地球上那些鼠目寸光的统治者总是缺乏想象力的,他们愚蠢而又贪婪,简直没法跟他们正常交流,所以湖心岛大概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的一种嘲笑,我相信父亲有这样的意图,不然他干嘛要建起这样一个火星呢?)
我循着父亲留下的线索朝着湖心岛的中心行进。
那里有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狡猾地隐藏在其他类似的石头中间,我曾无数次在梦里琢磨过它的样子,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捕捉。巴掌大小的石头,覆盖着蓝色的水晶岩藻,它们干枯之后就变成了青色,妈妈说我最适合穿藏青色的衣服,所以直到上大学结束前,她给我买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这个颜色,平均每年增补一到两件。这就是一种因果循环,我说不好到底是谁创造了谁,湖心岛还是我的童年外套。
接下来我会掀开那块石头。这个动作不需要去思考,我在梦中干过成百上千次,不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后来漫长的宇宙航行途中。石头揭开的时候我稍微做了停顿,仿佛是为了等待一个嗝,全身暂停,然后依次鼓动胸脯、脖子和嘴,吐出一口像气泡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就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消失了,永久性地,never more。实际上根本没有嗝,谁知道呢!
石头下面有个凹陷处,是父亲的坟包。
坟包很新,坟包里有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老者,看起来非常苍老的那种,看起来已经过了七十五岁。这是障眼法。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个耄耋老人,这是他的写照,同时作为一种态度。——当我们可以表达态度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会吝于表达。——这张老脸虽然看起来有些模糊,但是依稀还是能够辨认出是父亲。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位精明的人,这张脸是父亲,这张脸的主人应该就是父亲了。
父亲的坟墓是用一层薄土垒砌而成的,土是蓝绿色的,上面刻有一些奇异的纹路。我蹲下来仔细地打量着坟墓的纹路,我发现这个墓穴非常高,墓穴的四壁都是由岩石雕刻而成的。墓室里还有一副棺材,棺材看起来非常崭新,我猜测是一副新的遗像,棺材的左侧有一排手工的花朵形状的石雕,石雕的样式有点类似中古的那种祭祀的仪式,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势,看起来有一种威严。——同样的一种花招。
小时候我玩过一种万花筒,或者不如说幻灯片,它由一个花俏的长方形盒子和一个按钮组成,长方形的盒子上面有两个小孔,你可以将眼睛凑到小孔上往里看,同时按下它的按钮。你每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从小孔里看到一幅立体的图像:一个猴子模样的人拿棍子打一个姑娘,一个小孩挥舞长剑砍断自己的胳膊和大腿,一个瞎子在房子里乱撞,直到房子整个儿塌到他身上,或者是一个姑娘,在阳台上看月亮,阳台下面有一个眉花眼笑到人在对着她唱歌……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幻灯片没有声音,所以你就知道它肯定是假的。
同样的道理,我面前的墓穴也是一出幻影戏。按照我的设想,每一个阴错阳差打开它的人都会看到不同的景象,至于他能看到什么,全凭他自己喜欢。那么,此时此刻,我脑海中涌起的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在墓穴口喊我的名字,一声长,两声短,仿佛牧童的吆喝。
一道斜坡横在天空,用压倒性的姿态俯瞰着我,以及我所置身的墓穴。
出现了两个人,在石坡侧面的窑洞口,一男一女,是地球人的形象。
女人的身体被一团黑雾笼罩住,看不到她的样子,她的身体却不停地在晃动,晃动的频率越来越快,我甚至能听到她嘴里念叨着一句咒语,她的声音非常的沙哑难听,仿佛是一个男人在叫喊:"你快回来,不要再执迷不悟!快回来!"她的身体在晃动,但是我看不到她。我听不到她的声音,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她是在呼唤我。
她知道我要来这里吗?这和我预想的可不一样。
我起身走向那个洞。在我靠近的时候,那两个人就消失了,我猜想是投影,糟糕的把戏,和我一样幼稚,用来对付我实在太般配,就像两个臭棋篓子互相摆烂,我的手放在洞门上。
洞的另一侧是一片漆黑。
洞里传出诡异的笑声,我的妈妈,那是她的灵魂在发笑。
"儿啊,这是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你看。"母亲在笑,但是我看不到她。
我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想象不出来她原本的模样。
这下可以解释得通了。一个父亲,十有八九是一个不存在的父亲,一个我在想象中构思过好些遍也仍然意犹未尽的父亲。生日快乐我的儿子,这就是送给你的礼物。
我感到绝望。并且发现脚下的坡道在摇晃。我顺着斜坡摔倒,落入漆黑的深洞。
这次是我的朋友,开了半个多月的飞机,摔倒在火星灼热的灰尘里面——连一块整骨也没留下!
我打了一个马虎眼,当他跟我介绍火星登陆事项的时候,我正在走神。我琢磨母亲说要给我一个生日礼物是什么意思,毕竟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我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是哪天。
在宇宙旅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穿梭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最终必然弄坏你的生物时钟。然后呢,还会忘记自己的名字,或者伙伴的名字,比如说我,就完全说不上来我是谁我的同学又是谁。
我的脑袋上有一颗螺丝松脱了,并且掉下来,这是飞机落地碰撞的结果。所以我怀疑自己又丢掉了一部分的记忆。这同样是司空见惯的。
刚刚我打了个盹,也就是飞机坠毁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估计花掉了半个火星日,因为太阳从一头来到了另一头。我利用这段时间做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梦。
这是每次旅行间歇我必须要做的事情,重新整理剩下的记忆,看看还能剩下多少。这些记忆至少来自七个人,在周而复始的飞行当中,这些人陆续离开,就像我的同学那样,要么摔死,要么在某一个不适宜的地方窒息而亡,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卡在了通风管道里,活活被烤成了肉干。
随着最后一架飞机的坠毁和同伴的离世,我看我的旅行也该告一段落了。
这都是宇宙旅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血肉之躯的实在不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从一开始我就听他们这样哀叹,作为地球人,他们已经回不去自己的故乡了,几次战争之后,地球成为一片死地,哪怕你戴上防毒面具生活在地底下也没有用,“宇宙流亡者”,这才是最适合他们的名字。
时至今日,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已在宇宙中这样逃窜了多少年,残存的同伙恐怕也所剩无几,更为糟糕的是,我们也记忆也变得越来越少,作为人类的替代品,机器人也不能打保票可以永世长存。至于将记忆移植到机器芯片里,差不多只能算是垂死挣扎,就好像远古皇帝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面,痴心妄想罢了。
我继续回忆自己的生日,以及给我留下生日礼物的母亲的脸,眼前是一片浮动的灰白。梦境最后的那个黑洞仍然在原地大张其嘴,准备吞噬所有。我琢磨着也没那么容易,至少在电量耗尽之前,我还可以尝试再追回来一些记忆的碎片,在这火星上,梦里怎么说来着,属于我自己的“火星”——这个称呼终究还是让我心里打鼓,它似乎代表着某着虚妄,不然如何说是“我的”呢?——说不定哪天就被什么宇宙智慧发现呢,希望它们到时候还能搞得懂地球的语言。
👇查看更多:
